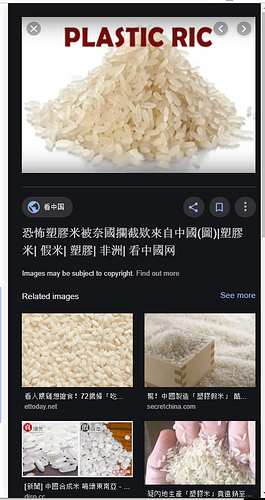十甲談俗:妇女队长槐香
糟木匠
妇女队长槐香总是笑呵呵的,有一對观音姐姐似的双眼。

十甲桥村一年种植两季水稻。每年的7月初到8月上旬的四十多天时间,是收割早稻,插晚稻秧苗的“双抢”季节。
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沉重的体力劳动让我觉得骨头架子都像要散掉了一样,只要一倒在床上,马上就能呼呼入睡。总是睡不够,那时心里总是想,要是能睡上一整天该有多好啊。
70年代初的十甲桥没有用上电,也没有任何动力机械,做农活完全依靠的是千百年前就有的农具和人的体力。村里曾经从公社借用过一台15匹马力的柴油机带动的水泵抽水,可以顶好多人用脚蹬水车,妇女队长槐香一提到柴油机就说:“那玩艺真神了!”
公社的王书记兢兢业业,常常串乡,不摆架子,喜欢和干活的社员聊天。妇女队长槐香扯住公社的王书记说:“看过公社农机站用柴油机带动的脱粒机,那机子真是威风。要是能让十甲桥村借用农机站柴油机带动的脱粒机,下次您到十甲桥来,把我家那只大芦花阉鸡杀了招待您。”
王书记批示同意将公社农机站15匹马力柴油机带动的脱粒机让十甲桥村使用两天。村里人捧宝贝似地拥着将柴油机和脱粒机抬进稻场。机器安装好了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抢插晚稻的时候,水就是命。在插秧的节骨眼上要是没有足够的水,那么半年的收成就没有了。听说在老年头里经常会因为放水,村子之间发生械斗,闹不好就会出人命,所以村里的男劳动力都去看护从水库放水。要防着别的生产队偷放分配给十甲桥村的水。

稻场上只有女人。妇女队长槐香拉住我,对队长说:“总得给我留下个能跳能踢的男人,木头能帮着看管柴油机,就让他留下吧。”
我在稻田里的热水烂泥中泡了一整个白天,已经累得连话都懒得说了。留在稻场,不用去挖缺口堵缺口的也好。妇女队长槐香点着名字要我留下,不用扛着铁锹像抓贼似地到水渠上去看着外村人。
脱粒机突突突地吼叫着,可对于我却像催眠曲。稻场上微弱的油灯盖不住夏夜天空中明亮的星星,记得美国有个叫马克吐温的作家说过:星星是月亮生的孩子,月亮就像青蛙产下无数的卵一样生出了很多星星。村子最南头土坯房子那家的小姑娘塌子,每天晚上总会用含糊不清的短舌头念着古老的儿歌:“月亮丫丫,星星伢伢,一天芝麻,沓成粑粑。。。”
一个大垛子打完了,开另一个垛子要几分钟,我靠着一堆稻草躺下去,强睁着沉重的眼皮望着星空。满天里挂着的那些“月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看着稻场上这么多会生孩子的女人。不知怎么地突然想起来妇女队长槐香常说她生孩子容易,就像拉大便一样,孩子就生出来了,不会像别的女人那样要死要活地叫爷叫娘。
槐香十八岁那年嫁到十甲桥来,在娘家,槐香是老大,下面的三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是她帮着妈妈带大的。槐香六岁的时候就喂弟弟妹妹吃东西,八岁时开始去上了两年学,後来就没有再上学了。只读过两年书的槐香,干起活来里里外外都能应付,又肯帮助别人,所以当上了妇女队长。
闪闪烁烁的星空将我疲倦的身子带起来飞,飞,飞,飞到很远,很安静,没有什么感觉的地方。那里有儿歌里唱的星星般的白芝麻,芝麻撒在月亮上做成了老大老大的粑粑。
一只狗走过来舔我的脚,我试着将狗踢走。很奇怪,我的身体是那么轻,轻得可以满天飞,但是腿却好像不是我的,抬不起来。我没有踢到狗,狗却知道我想踢他。我有了神通,我的眼睛能看到狗的心里在想什么。狗也和我一样有了神通。。。我一点也不在乎这么诡异的情形会发生。我想更加用力地踢狗一脚。狗看到了我的心思,往我的脚上咬了一口。
醒过来了,妇女队长槐香用手中的扬叉--一根前端分叉的树枝做成的,用来翻稻草的手工农具--不算太轻地敲我的脚。我仍旧迷迷糊糊,没有听明白槐香在说什么。她见我醒了,就不说了。

妇女队长槐香其实只比我大四岁,已经有两个孩子。在我的感觉里,大四岁的女人比我大很多,应该和我妈妈是一辈的。
我一直很尊敬妇女队长。她干活都是生龙活虎的,现在看起来也是一脸的疲乏。大家都很累,连槐香都显得这么疲乏,还有谁能不累呢?
我慌忙地从草窝里爬出,站起身来。几根稻草从我的头发上垂下,身上沾了一些稻草,顾不上整理身上沾着的稻草,连忙接过槐香递给我的扬叉。她说,刚才开新剁的时候,需要给柴油机加一桶冷水,她本想让我到水塘里去打一桶来,看到我慢慢地倒进稻草窝,就自己去打水。水塘边的泥土湿漉漉的,她脚下一滑,差一点跌倒在水塘中了。
睡境中的静谧,清香,轻逸都立即离我远去了,柴油机的噪吼,自己身上的汗味,我克服着眼皮的沉重,看着因为跌了一交裤腿上和衣襟上沾着烂泥的槐香队长,迫使自己赶快回到现实中。
槐香对我很好。她会将她正吃着的米粑粑撕下一大块,两个指头钳着塞进我的嘴里--那次我在水稻田里薅草,两只手上都是泥。她问我好不好吃,她问我城里有没有这样的米粑粑。她告诉我,这次做米粑是王书记帮她买的白糖,不是糖精。
在评工分的时候,队长说我的个子小力气也小,每天应该比别人少半分。槐香说我干活实在,不偷懒,所以不能比别人少。她总是护着我。她留下我在稻场上,本来就是指望我能做一些男人该做的事情。我却睡觉了,让她去提水,还差一点跌进水塘里,我很後悔自己熬不住,受不得累。我是留在稻场上唯一的一个男劳动力,应该更尽力一点的。

我一边干活,一边偷偷地看妇女队长,她脸上经常挂着的笑容没有了,观音姐姐般的脸上没有笑容,似乎在强忍着什么。大家都很累,那是双抢啊。前天开田头大会时大队支书说:“同志们,现在是如马的‘双抢’,什么是‘抢’啊?淹了水才要抢,失了火才要抢。。。老话说,一年三十九日忙,一天要办九天粮。现在是“抢”的时候,是拼命的时候。”我一边想一边扭过头再看看槐香, 她平时是个非常豁达的人,不会和别人计较的,现在看她紧皱着的眉头和不高兴的脸,我心里很不自在。
我依旧在强撑着,迷迷糊糊中干完了活。大家说,好了,吃消夜了--新鲜米饭,咸菜汤。
我不想吃,只想睡觉。。。。。。
第二天起床,还是觉得困和乏--只睡了四个小时。漫天里,月亮的孩子们仍旧在眨巴着眼睛,东方尚未发白,队长就又吹响了哨子。人们集中在稻场上等候队长派工。村北头的箍匠说, 槐香昨晚干活不小心扭了一下,先是见红,上床後不久便小产了。
槐香在家里休息了两天就又下地了。 两个月後田地里的农活轻松了一些,县里下达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指令。槐香对其她的妇女说:孩子还是少生几个的好。一个不算少,两个就够了,有三个的要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一定不能再生再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