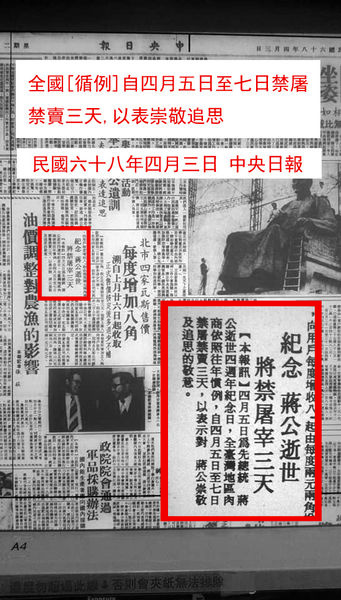小弟剪貼網上文章如下:
台灣軍不是台灣人組成的,而是日本帝國陸軍台灣駐屯軍的通稱,兵源是日本內地抽調的,大部分是九州一帶。
台灣人日本兵被徵調的都是軍屬軍伕,負責修建機場挖戰壕等體力工作…
台籍日本兵一直到1943年底才有機會在南太平洋的島嶼上參與戰鬥任務,但有許多台籍日本兵被指派去管理日本正規軍人不屑做的戰俘營看守工作。
二戰結束,虐待戰俘的日本二級戰犯有很多是台灣籍和朝鮮籍,被處以絞刑。
反而日本上司脫罪,聲稱我們日本人不會幹那種事,撇清責任。
台籍日本兵是時代悲劇。
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從未有台籍日本兵受銜軍階在大尉之上,最高為中尉醫官,而戰鬥人員最高為飛行中尉。陸軍戰鬥單位幾乎無尉官之上的台籍日本兵。
二戰時台籍日本兵(軍屬、軍人)共207083人,朝鮮共242341人。
當時台灣總人口600萬,朝鮮2100萬,所以台灣出兵比率竟高於朝鮮3倍以上,可令人訝異的是,台灣兵都是小兵,軍階最高的是少佐(鍾謙順)。
但朝鮮人任日軍中將的有6人(李垠、李秉武、洪思翊、魚潭、趙性根、趙東潤),少將2人,大佐3人,中佐3人,少佐1人(相當於少校),大尉1人,中尉1人。
日本陸軍升遷階級森嚴,尉官幾乎都要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校級以上高級軍官都要陸大畢業。
台灣人在當年似乎是很難被接受讀日本軍校。
分 - 隔 - 線
現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把佔人口百分之五的外省族群,撇開不說。
約有三成,即六七百萬的客家人。
這六七百萬的客家人,乃是中國漢朝滅亡後,五胡亂華,迫使中原氏族為避戰禍,而大舉南遷。就遷居客籍於江西、閩西與粵東,形成所謂的客家人。
換句話說,客家人就是中國漢朝的遺民。明清之時,客家人又大舉遷居台灣。也就是說,現在的台灣人口中,有六七百萬的漢朝遺民。
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口中,也不止是有三成的漢朝遺民。更多的,則是中國唐朝的遺民。約有一千四百萬,佔比高達總人口的七成。
即所謂的「河洛人」,也就是閩南人。「河洛人」的形成有二。
一是唐初,為平閩南百越蠻獠嘯亂,徵調河南光州固縣府兵,前往征閩。
繼之開漳聖王陳元光,在閩南開設漳州,屯田開墾。二是唐末,同樣是來自河南光州固縣的民兵,南逃閩南泉州。繼之開閩聖王王審知,一統八閩,於唐亡後,建立閩國。
二次從中原河洛來的軍事移民,就形成了後來的「河洛人」。
儘管唐朝滅亡,但河洛人千年來,仍始終自稱「唐人」「唐山人(來自大唐盛世江山之人)」或「河洛人」。因河洛人的本身,其實就是中國唐朝的遺民。
明清之時,唐山過台灣,河洛人又遷居台灣。於是現在的台灣,約有一千四百萬的唐朝遺民。
總括而言。台灣的漢唐遺民,也就是客家人與河洛人,加總起來,超過總人口的九成以上。
這九成的漢唐遺民的子孫,說自己不是中國人,實在是:睜眼說瞎話,或是腦殘囈語。
分 - 隔 - 線
一位屏東潮州人潘天元,他擔任日本軍伕、國府軍醫務員、中共人民解放軍。
參加過「二次大戰」、「國共內戰」、「抗美援朝戰爭」,短短幾年當中,以三種軍人身分,參加三種戰爭,這些都不是他自願的
1946年2萬餘名台灣熱血青年,出征!航向中國,為國共內戰前進!
1946年年6月70軍整編成70師,轄139旅、140旅、141旅。
一萬多台灣兵,12月開赴徐州,參加過魯西南、徐蚌(淮海)戰役。
到了8月時62軍整編,轄67師、151師、157師和獨立95師。
又「綱羅」幾千台灣兵,9月開赴華北,參加過遼瀋、平津兩大戰役。
分 - 隔 - 線
國民黨70師於1947年在山東戰敗。
投效整編七十師的台灣兵,則大多數犧牲於山東金鄉的「羊山集戰役」、河澤的「柳林集戰役」及徐蚌會戰的「陳官莊之役」(隸屬邱清泉的第二兵團)。
70軍開往山東,先後參加了巨(野)金(鄉)魚(台)戰役和魯西南戰役。
在魯西南戰役中,剛剛從台灣基隆海運徐州的整編第70師所屬的整編第140旅,從徐州出發,經豐縣、魚台縣馳援金鄉縣城。
70師師部和第140旅被晉冀魯豫野戰軍全殲,中將師長陳頤鼎、少將副師長羅哲東等被俘。
分 - 隔 - 線
「趙子龍師」獨立95師。
常山趙子龍如雷灌耳,能取這個名字當然很不簡單,但其原因卻無人知曉,現在就給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國民革命軍獨立九十五師,又稱趙子龍師。源自馬鴻逵的私家軍隊“安寧軍”,本源於其祖父馬千齡。
馬千齡在同治年間先參加反清起義,後率部降清當官,私家軍隊也變成了國家的正規軍。
由於馬家軍都是西北健兒,身體強壯,勇敢善戰,槍術刀術騎術嫻熟,加上家族勢力和宗教信仰的影響,特別是戰鬥的鍛鍊,很快成為戰鬥力極其頑強的馬家子弟兵。
34年整編時調入大量的黃浦系中下級軍官,由羅奇接任第三任師長,任此職長達6年之久。因此該師也慢慢從地方雜牌變成了准中央嫡系。
西北馬家軍非常善於近距格鬥,儘管後來該師西北人越來越少,這一傳統卻保留下來。
95師極為重視白刃搏鬥的訓練,從軍官到士兵都是拼刺刀的好手,這一點給很多國府高級官員留下深刻印象。因長期駐守河南南陽,該師又被稱為「當陽部隊」。
抗日軍興,參加了豫北游擊戰,徐州外圍作戰,第一、二、三次長沙會戰,長衡會戰等。
在第二次次長沙會戰中,283團一個連在橫田鎮一個樹林裡與日軍荒木支隊一個大隊(也相當於一個連)近距離遭遇。
日軍們退掉子彈抬著38槍高叫著沖了上來,國軍士兵們毫無畏懼迎上去,一場激烈血腥的白刃戰進行了近一個小時,殺紅了眼的雙方竟然都無退意,直到一方的人全部倒下。
日軍的白刃戰極其厲害,連善使大刀的西北軍也很少占到便宜,可是這次戰鬥的結果是我方傷亡六十多人,日軍被格斃九十四人,一個大隊幾乎被全部殺死。
據日方記載,後日軍部隊所發現屍體極少槍傷,大部為白刃格殺,大隊長上原被三把刺刀釘在一棵大樹上。此戰轟動了整個戰區,加上95師在整個會戰的出色表現,「當陽部隊」「趙子龍師」從此叫響!
日軍中熟讀三國者眾,因此「趙子龍師」也在日軍中很有名氣
抗戰勝利,95師赴越南受降,接收台灣,使該師官兵頗感光榮。
日軍第72師團駐地在善化,台灣省軍事接收委員會指令陸軍第62軍第95師奉命實施軍事接收任務,該支中國軍隊從12月1日開始接收,12月15日接收完畢。
塔山阻擊戰
1948年9月,遼瀋會戰打響,獨立95師奉令加入國軍東進兵團,自華北開赴東北,進攻塔山,企圖支援錦州范漢傑部,會同西進兵團廖耀湘部夾擊解放軍。
此時,羅奇剛被南京政府晉升為中將,擔任總統華北戰地視察官,負責華北戰事,隨東進兵團督戰指導。
羅奇到達塔山前線後,立即以老師長的身份召見獨立95師全體中下級軍官,要他們以傳統的強悍作風攻下塔山,並拿出大量金圓券組織了敢死隊。
1948年10月13日,在塔山前線,獨立95師的全體官兵在戰前動員後,全師連續高呼“沒有95師攻不下的陣地”,就發動了整營整團的集團衝鋒。
10月13日凌晨四時國軍開始發動進攻,國軍綽號「趙子龍師」的獨立第95師替換暫編第62師投入戰鬥,沿塔山至錦州公路主攻塔山左右兩翼陣地,並動用海軍重慶號巡洋艦火炮支援(但是重慶號艦長藉口視野不佳未有力配合陸軍)。
獨立第95師攻擊時採用波浪式的衝擊戰法,戰鬥極其慘烈,國軍攻擊部隊遭到共軍集中火力射擊,攻勢受阻於東北野戰軍陣地障礙物前,當日,國軍傷亡1,245人,東北野戰軍傷亡1,048人。
塔山阻擊戰激戰過程中,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向該戰役指揮官第二兵團司令員程子華命令「我不要傷亡數字,我只要塔山!」。
10月14日拂曉五時,國軍集結5個師的兵力再次進攻塔山。
上午,國軍反覆衝鋒,塔山陣地曾九次易手,最後仍在東北野戰軍控制之下。
國軍傷亡三千餘人。
15日凌晨1時,國軍對塔山東北野戰軍陣地實施突襲突破前沿陣地,拂曉東北野戰軍集中炮火轟擊並發動反擊,國軍後撤未能攻下塔山。
這種戰法固然強悍勇猛,但相當愚蠢的。
至內戰後期,國共雙方主力部隊的裝備相當,即使不用重武器,僅靠輕步兵火力的密集封鎖即足以擊退純步兵組成的集團衝鋒,何況獨立95師不僅兵力不占絕對優勢,而對手又是東野五虎之一的第4縱隊(後改編為41軍,塔山防線指揮員程子華、吳克華、李天佑)。
結果可想而知,獨立95師雖然憑藉作風強悍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多次突入解放軍塔山陣地,但在解放軍堅決反擊之下,始終不能越雷池一步。
只經過兩天的較量,獨立95師就傷亡了三分之二,國軍獨立第95師傷亡慘重,15日由第21師替換。
最後縮編成3個營撤回華北,駐防塘沽。
15日,天降大雪,由於東北野戰軍攻占錦州的消息傳來,10月16日國軍就地轉入防禦,塔山阻擊戰結束。
62軍、獨立95師於1948年在東北戰場戰敗。
投效陸軍第六十二軍及獨立九十五師的台灣子弟兵,大多數都橫屍於東北錦西的「塔山戰役」。
1946年2萬餘名台灣熱血青年,出征!航向中國,為國共內戰前進!
在冰天雪地、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甚至在嚴苛的「戰時戰地軍律」監控下,為中華民國、為國民黨政府出生入死。結果十之八九,一去不回。
徐蚌會戰後隨國民黨政府平安撤退返台的台灣兵只有四百多人。
分 - 隔 - 線